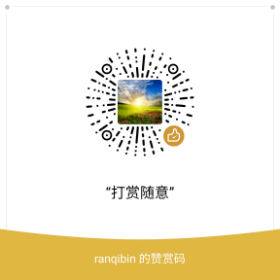简云斋闲谈丨中国人发现美洲:特立独行的历史学家卫聚贤及其行事
是中国人发现了美洲:特立独行的史学家卫聚贤及其行事
现在的课本上都讲美洲是哥伦布发现的。故事是这样的:1492年8月3日,哥伦布在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的支持下,据说带着给印度君主和中国皇帝的国书,率领三艘百十来吨的帆船,从西班牙巴罗斯港扬帆出大西洋,直向正西航去。经70昼夜的艰苦航行,1492年10月12日凌晨终于发现了陆地。当时他以为到达的是印度,所以管那些土著人叫“Indians”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启了世界殖民史的全新时代,影响至巨。
近代以来却有很多人提出第一个到达美洲的不是哥伦布,而是中国人。他们认为不仅第一个到达美洲的是中国人,而且有大量的中国人在哥伦布之前曾经去过美洲。此说的始作俑者可以追溯到章太炎氏(章太炎作有《法显发现西半球说》)。民国时期的卫聚贤(1899~1989)则更大倡其论。自兹以后代不乏人。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最早到达美洲的是中国人,并提出“玛雅——中国文化连续体”之说(张光直《考古学专题六讲》,文物出版社1986)。而连云山《谁先到达美洲——纪念东晋法显大师到达美洲1580周年》(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)更是专门考证法显的航向、航线,论证其曾到达美洲。
在主张中国人最早到达美洲的学者中,卫聚贤很值得进行介绍。卫聚贤系考古学家、历史学家、古钱币学家,解放前曾任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长、吴越史地研究会总干事等,主持发掘过南京明故宫遗址、汉汾阴后土祠遗址、嘉陵江北岸汉墓等。1951年卫聚贤到香港,后又到台湾,曾任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研究员、台湾辅仁大学教授等。
卫聚贤1969年出版《中国人发现美洲》一书(香港),1975年出版《中国人发现美洲初考——文字与花纹》(提出秘鲁土著人是南宋人后裔),都倡导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说。卫先生不光撰文说中国人发现美洲,他还亲自带队实践。1974年,75岁的卫聚贤先生和一群爱好者乘坐仿照汉代的木船,带着仿照汉代的食物,船上也不配备现代化仪器设备,从香港起锚一直驶向浩瀚的太平洋,以模拟证明早期中国人到达美洲的航行。不幸的是,船儿走到快到彼岸一百里左右失事了,以至于九尺竿头,功亏一篑。不过船虽然失事,但船上的人得到营救,幸免于难。
卫聚贤不光撰文《中国人发现美洲》(1969,香港)、《中国古代与美洲交通考》,还撰有《中国人发现澳洲》。这就是说中国人除了居住的亚洲、已经接触过的欧洲和非洲之外,还发现了美洲和澳洲。唯一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卫先生没有撰文证明中国人发现南极洲。
终其一生,卫聚贤先生提出的论点不仅让人吃惊,而且这些让人吃惊的论点数量繁多。他不仅提出中国人发现美洲、澳洲,他还提出“龙就是鳄鱼”;他怀疑屈原的存在,认为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屈原这个人,所谓“屈原”就是贾谊“冤屈”的改字颠倒;他1929撰文说老子、墨子、扁鹊等都算是印度人(见:《墨子老子是印度人考证》,《认识周报》第2期;《墨翟为印度人说》,《古史研究》第二集,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。其中《墨子小传》说“产生地究为印度或亚剌伯亦不易定”)。他还认为《山海经》也是出自印度人之手。看来卫先生是和印度人干上了!
除此以外,他的种种匪夷所思的看法还包括:古代中国人曾经步行经过白令海峡;他不仅认为东晋高僧法显(约337-412)在哥伦布之前到达过美洲,而且还认为哥伦布之前早已有百余中国人到过美洲,这些人是:殷遗民,孔子,张衡,慧深等,甚至还有古惑仔李白、胖美人杨贵妃女士等等。
从上面的论点可以看出卫先生研究的理路确实是大胆假设,惊世骇俗,语不惊人死不休。
从学术观念上看,卫聚贤和顾颉刚一样是疑古派的代表之一,是一个勇于挑战传统的异端。他自己一方面反对传统,说“传统是懒惰的代名词”;但同时他又是一个不自觉为“传统”服务的人。他提出中国人发现美洲、发现澳洲,都是为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着力。
在学术成绩上,卫先生撰写的《中国考古学史》(1937)多次再版。《古史研究》(第一、二、三集)也曾多次再版。他还撰写有《十三经概论》、《古钱年号索引》。除此以外他还撰写了中国第一部《历史统计学》,用数学统计法计算《春秋》和《左传》的叙事频度,发现《春秋》记事最丰富的年代为孔子卒前的九十余年中。依此类推,他计算出《左传》记事最丰富的年代,并选择其最高点,减去九十年而得到《左传》著者的年代,应该是在周威烈王初年,即公元前425年的稍后几年中。卫聚贤先生的文学、戏剧、民俗研究有《小说考证集》、《雷峰塔》、《杨家将考证》、《薛仁贵征东考》、《中国的帮会》、《红帮汉留人物故事》、《袍哥入门》等等。
卫先生的个人经历也足堪大书特书。他幼年历经不幸,三岁丧父,四岁母改嫁,时常受继父打骂。19岁时借同学卫怀彬的毕业证才算考入山西省立高等商业学校(这在今天就要算文凭造假了)。后来去北京考取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届研究生,导师为国学大师王国维。卫聚贤毕业后专门从事考古、历史等研究。30年代以后他曾涉猎商业界,得到孔祥熙的支持,出版过《中国财政史》、《中国商业史》、《山西票号史》等。卫先生后来还组织筹建吴越史地研究会,主编《说文月刊》等。他还曾首次提出“巴蜀文化”这一名称。
卫聚贤一生穷困,就是后来在香港和台湾也没有过过宽裕的日子。他因年轻时穷困,写字一直写得又瘦又小。但他后来体格却长得比较大,这样他人大而字小,人胖而字瘦,形成鲜明的对比。他生活非常节俭,给人写的信都没有超过两页的。他自号卫大法师,化名有韦痴子、鲁智深等。他自认“我是一个喜欢用头脑幻想的人,不是写就是想,不能让它闲着‘自腐化’。”他有一个警句:“猛发财是腐化的前奏,享清福为死亡的等待”。他既饱受苦难,又性格倔强。他一生穷困潦倒,但不管他人评说。他的种种高论也不被学界承认,而时常受人嘲讽贬损。商承祚说他“治学同作文章,都不求甚解,写了就罢,说完就算,信不信由你,对不对在他”。然而他也确有真才实学,苏雪林说他读书之博,国内恐无第二人。张光直则说他“一生以出怪论为著,我一生所最钦佩的读书最多的人就是他”。
卫聚贤先生种种特立独行的学术成绩和私人活动还有很多,可惜他的名声不为一般人所知晓,以至于几乎在历时中湮灭无闻了。
(2010年12月于天津)